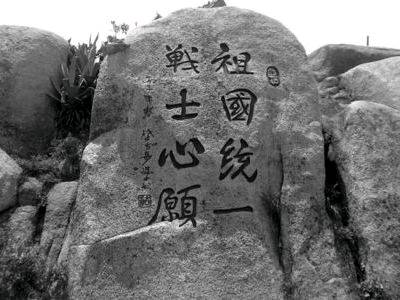
|
| 將軍山也留下了軍演戰士心中的願景 |
2008年的兩項公投都沒有通過,馬英九也登上了大位,但是台灣人民對於中國人的認同並沒有增加,支持台灣獨立的卻愈來愈多。這說明了,馬英九即使贏得了選舉,但是李登輝的論述,以及他所創造的結構漩渦卻是愈來愈強。北京也是這個結構的共業一分子而不自覺。
北京應該瞭解,近十餘年來,台灣人民只有兩種選擇,不是選擇李登輝的論述,就是選擇北京的論述。北京“不願意接受中華民國”的論述給予泛綠無限大的操弄空間,連泛藍都擋不住。北京如果不能及時修正補強,提出新論述,民進黨永遠有利用的機會,他們只要不停地問,台灣不是一個國家是甚麼?台灣是不是北京的地方政府?這些問題只要一日不停,兩岸的情感與認同就繼續拉大。這是兩岸的悲劇,可是它卻真實地存在著。
如果說,從1993年開始,兩岸進入論述的對決,北京的“一個中國”與台北“台灣主體性”的對決,雙方都是輸家,台灣陷入意識形態的內耗,經濟發展裹足不前;大陸沒有得到台灣人民的認同,兩岸認同快速折裂。北京與國民黨應該認真提出一套能夠擺脫或吸納李登輝的論述,可以讓兩岸都可以雙贏的論述邏輯。
沒有核心共識就沒有互信
從1996年以後,台灣學術只在政府的引導下開始研究如何建立信心措施問題,但是總是在技術與程序問題上著手,完全沒有碰觸到核心。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提出各種建立互信的方案。包括:第一、宣示性措施,例如兩岸宣示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第二、溝通性措施,例如建立熱線等危機處理機制;第三、透明化措施,例如公佈白皮書、軍事演習前通知對方、資料交換、觀察演習等;第四、限制性措施,例如限制邊只的軍備與數量;第五、查證性措施,例如空中檢查與實地檢查等。二是強調“先易後難”、“先簡後繁”、“先外圍後中心”等步驟的秩序性。即主張兩岸可以從簡單的地方開始,透過相互信任的累積,逐漸再來處理最核心的“一個中國”問題。
必須要很坦率地說,這樣的思維只是把世只各國“建立信心措施”的內容與方式照抄一遍,而沒有深刻思考問題的本質。我想問的是,我們要追求的是一個真正、可長可久的互信,還是一個為了處理目前可能的衝突,而建立的互信?在我來看,前者才是真正的互信,後者只是為了各自利益的權宜之計。
我們就回到“信心建立措施”的原始理念,看看它是如何形成。“信心建立措施”的概念最早出現於1975年的“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所達成的“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就是“信心建立措施暨安全與裁軍文件”。這裡不談文件內容,要問的是,為甚麼冷戰期間東西歐國家願意簽署這份代表著建立互信的最終議定書文件?
二次世只大戰過後,東西歐的疆只出現了一些變化,德國分為東西德兩個國家,俄羅斯與波蘭的疆只西移。二戰後緊接著就是冷戰的開始,一直沒有一個“和平條約”來處理戰後的領土與主權問題。到了1975年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東西歐終於確定了戰後的主權與領土,因此,“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在意義上其實就等於是二戰後歐洲的“和平條約”。在這個“和平條約”中,蘇聯與華沙組織得到了西歐對於其主權與領土的確認,因此才願意與西歐國家進行“信心建立措施”。簡單地說,由於東西歐對於核心問題已經有了共識,才有互信機制的產生。
這個簡單卻是重要的故事告訴我們,如果兩岸不能夠在核心問題上取得共識,兩岸不容易建立真正的互信。1993年兩岸可以進行“辜汪會談”,因為至少台北在國統綱領中宣示了“一個中國”立場。又為甚麼海基海協兩會自此以後協商逐步破局,關鍵當然在於台北方面逐漸偏離“一個中國”的軌道。北京在主觀上不接受“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論述,在台灣政客操弄下,也間接助長了這個軌道的偏離。
海基海協兩會所建立起來的機制,本身就是一個“互信機制”。從它運作迄今可以看得出來,它是異常的脆弱。如果對於“一個中國”及其內涵沒有共識,那麼所謂的“互信機制”將會淪為是技術性的安排,不可能依靠它們建立真正的“互信”,它們充其量只是個聊勝於無的措施,宿命地在“建立-破裂-修補”中循環發展。
不同於東西歐經由“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達成共識。西歐各國從1950年代開始推動共同體。維持與推動這個共同體的精神就是彼此對於“和平”的共識。在西歐各國眼中,“和平”已經不僅是一項“政策”或“手段”,更是一項“價值”與“信仰”。由於歷經第一、二次世只大戰,死傷了千萬人後,歐洲人終於深刻地體認到不應該再有戰爭,因此,他們第一個成立的共同體就是“煤鋼共同體”,由成員國共同來管理戰爭所需要的煤與鋼。反觀兩岸,“和平”迄今為止,還僅是一項“政策”或“手段”而已,離“價值”或“信仰”還遠得很。北京方面,在追求和平統一時,仍舊不放棄使用武力;台北方面在呼應和平發展時,也不忘大量購買軍備。何以至此?或許是仗打得還不夠、內戰所留的血還不足、親人的傷痛還不夠深到足以喚醒兩岸政府與人民。北京保留最後使用武力權,台北期望有台獨的選擇機會,以至於雙方沒有認真地感受到需要建立真正“互信”的需要。
要建立互信,絕不能不提“一個中國”,也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中各表”。“各自表述”源於“相互信任不夠”。兩岸應該追求的是“一中同表”,即共同對於“一個中國”這個核心問題進行雙方都能接受的表述。唯有如此,兩岸才能建立真正的“互信”,也唯有如此,“和平”才有可能從“政策”或“手段”轉為“價值”與“信仰”。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大家都是中國人,自然沒有中國人打自己兄弟的道理。
沒有自信就沒有互信
一個沒有自信的人是不容易相信他人的,國家也是如此。隨著中國大陸近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北京愈來愈能夠展現出它的自信。面對詭譎多變的世局、逐漸走向分離的台灣,北京仍能堅定地主張“和平發展”,這就是北京自信的表現。社科院台研所願意與兩岸統合學會就“一中三憲”進行討論,而不以“一中一憲”做為前提,不就是自信的表現嗎?
反觀台灣,網路戲稱“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卻是十足傳神。意識形態民粹式的動員讓台灣內耗十餘年,迄今沒有停止跡象。北京的論述成為泛綠可以操弄的代罪羔羊。1970年代以前,台灣還有與北京“爭正統”,“爭誰才是真正中國”的氣魄;但是在與美國斷交後,處於劣勢的台灣逐漸失去自信,不再敢多談“一個中國”。在北京獨佔“一個中國”的論述下,台灣也被迫選擇新創論述。在北京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時,台灣方面就必然用“強化台灣主體性”來武裝自己。簡單地說,對北京的“受威脅感”助長了“台獨”。“台獨”與“獨台”是一種“逃”的哲學,“逃”起因沒有自信面對挑戰。
北京雖然已有較多的自信,但是還是沒有接受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的自信。北京擔心,如果接受中華民國的法理存在事實,是否等於接受了“兩個中國”。兩岸目前的確在法理上仍處於內戰的延續,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上也確實處於優勢地位,但是對於“和平統一”仍然缺少信心,因而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權力。北京的現有統一論述是建立在中央統一地方,缺少用兩岸平等方式追求統一的自信。“手把青秧插滿田、退步原來是向前”是一句禪詩,“有捨才有得”是一句古訓。北京可能需要瞭解,只有強者才有讓步的本錢,讓步對強者而言是一項美德,對弱者卻是一種屈辱。在兩岸問題上,北京應該把台北當平等的兄弟看待,共同追求胡錦濤所說的“復歸統一”。
台北也必須重拾自信。幾乎所有來過台灣的大陸朋友都認同台灣保留了更多的中國文化,從台灣人民的生活中,看到了中華民族也可以享受文明的公民社會。台北不要總是看到一個打壓台灣的“政治中國”或可能消化台灣的“經濟中國”,而應該看到是正在巨變的“社會中國”。台灣人民應有信心與勇氣幫助社會的中國走得更開放、更美好。堅守“一個中國”不僅是政治上的原則,更是一種權益上的責任,堅持“一個中國”不僅是我們對歷史負責,更是我們擁有中國未來的權利。
兩岸都需要自信,台北需要有堅持“一個中國”,才能引導中國發展的自信,北京需要有透過“兩岸平等”,更容易走向統一的自信。兩岸如果能夠重拾自信,互信自然可以水到渠成。
結論:如何讓互信不可逆轉
在北京研討會時,北京與會者擔心的問題是,兩岸互信是否會發生逆轉?北京對於台北的民主機制是擔憂的,他們擔心,台灣會否突然有一天因為換了政黨,把以前兩岸簽署的“和平協定”全部推翻,或者來個公投,迫使台灣走向獨立?
北京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邏輯上說,逆轉絕對存在著可能,因此我們應該思考如何讓這個逆轉不發生。第一個作法就是和平協定的內容必須合乎現實,並且是雙方都能接受的。對於北京來說,是“一個中國”;對於台北而言,是“憲政地位”。對北京而言,接受台北為一個“憲政秩序主體”,只是接受事實的現狀而已,但是可以徹底消除台獨的訴求與政客的操弄;對台北而言,接受“一個中國”,只是尊重自己的憲法而已,但是可以避免繼續內耗與可能的兵凶戰危。兩岸看似讓步,其實都沒有讓步。一個兩岸都可以接受的“和平協定”才有可能得到雙方人民支持而成為事實,“和平協定”對雙方的規範才是真正的紅線。
第二個作法是對“一中原則”做出不可逆轉的安排。在“一中各表”的架構下,台灣如何表達“一中”,取決於台灣的內政,但是當兩岸簽署“和平協定”,雙方均做出“承諾不分裂整個中國”時(請參考〈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芻議〉《中國評論》,2008年10月號),維持“一個中國”原則就已經是雙方共同的責任與義務。因此,“和平協定”,這個可以稱其為“第三憲”的基石之協定,本身即因而有了不可逆轉的約束。(請參考〈一中三憲〉《中國評論》,2009年9月號)
第三個作法,就是如何努力創造其它結構來讓其不可逆轉。不努力經營,任何再好的結構都會出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岸統合”、“兩岸共同體”、“中華共同體”,或“一中共同體”,不論名稱為何,都是值得兩岸努力推動的。(請參考〈共同體〉《中國評論》2009年10月號)
走筆至此,讀者或許可以更清晰瞭解,“一中三憲”應該是未來“和平協定”的基本原則,它可以讓兩岸的互信透過協定約束而不再逆轉。它不同於東西德透過基礎條約中的“一德各表”來建立互信,也不同於東西歐透過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中的“相互尊重主權”來建立互信。它在北京所強調的“一個中國”與馬英九所呼籲的“正視現實”中找到了交集。“一中三憲”是兩岸建立核心共識的互信基礎,“和平協定”是這個互信基礎的機制。這個互信機制兼顧了原則與現實,更包含了理想。
謹以此文,嘗試為胡錦濤先生所主張的“建立互信”做一詮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11月號,總第1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