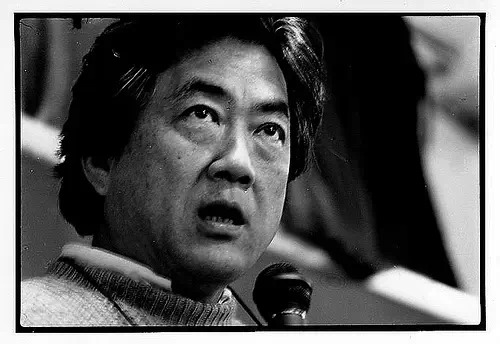|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 | |
| 汪輝: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 | |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
或許有人會問:沒有“統派”又怎麼樣?我的回答是:“統派”的誕生是對“獨派”潮流的回應,其衰落只是社會潮流發生轉化的標誌而已;所謂“統派”式微並不代表其徹底消失,毋寧處於消長起伏的消與伏的歷史階段而已。在這個階段中,由於體現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歷史聯繫和情感聯繫被人為壓抑和政治扭曲,台灣島內難以形成真正的社會團結,裂隙和情感傷痕將長久存在;沒有“一”,所謂“多”將因缺乏共同平台而陷入孤立、疏離和持續隔絕的境地,兩岸關係也會因為缺少能夠相互溝通的橋梁,難以形成改變區域霸權構造的共同力量。由於地緣、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台灣與大陸存在著難以分割的經濟、政治、文化聯繫,試圖脫離大陸解決其內外危機是不可能的。試圖將兩岸關係懸置起來談論台灣認同,台灣內部和區域內部的政治斷裂就是不可避免的。換句話說,“統派”的式微不僅是兩岸問題中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而且是台灣內部政治危機的一個部分,也是亞洲區域改變冷戰和後冷戰格局的關鍵所在。中共用連戰、宋楚瑜這些國民黨二代作為代表。他們屬於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的一代,但還綿延著內戰和冷戰時代的一部分印記(也就是“右統”的印記),加上改革時期他們在兩岸交流中的新角色,將他們作為聯絡對象是自然的,但把他們當做“統”的象徵,內容已經是空洞的,因為他們對美日的支配結構習以為常,對年輕一代也毫無影響。這個遊戲已經到了快結束的時候了。兩岸關係和台灣內部關係都處於由於“統派”消失或者說“獨台”成為主流而產生的困局之中。 在台灣島內,比較明確意識到這一點的其實是辜振甫及其周邊人物——這裡不談他們的複雜的歷史背景。我順便講個小故事,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的1999年,我去參加辜公亮基金會為《嚴複合集》出版而組織的一個嚴複學術討論會。我那時在社科院工作,申請入台證手續複雜,邀請方來電話表示要去幫我疏通關係。放下電話後不到一小時,國台辦就給我打電話,要我直接去拿入台證。到了台灣,辜振甫秘書來機場接我,方才知道他們使用了直通電話。辜振甫的秘書在路上跟我說:辜先生這一代人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再也走不下去了。我問為什麼。他說:導彈危機之後,辜振甫於1998年10月訪問上海和北京,10月15日在上海新錦江飯店白玉蘭廳,汪辜在一種“家庭式的氛圍”中會談,達成四點協議。談判其實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汪道涵在歡迎宴會上就說:促進兩岸政治談判是現階段全面推進兩岸關係的關鍵。汪道涵和辜振甫單獨一桌,品茗而談,隨員位置相距較遠。午飯吃完了,形成了四點共識,緩解了那一次台海軍演之後的緊張局勢。但辜振甫回台後,台灣方面並未沿著四點共識的精神向前推進,反而不斷放話,設置政治談判的障礙。辜振甫的秘書說,那次四點協議之後,辜振甫自己說,從現在開始,我們能做的都做過了,到頭了,再也不可能了;要有新花樣,就要換人了。當然,李登輝之後的變化恐怕也超出他的預估。其實,從國民黨官方來看,國統綱領正式的完結是在1996年前後,李登輝已經在為“兩國論”出台做好鋪墊了;所謂“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也可以說是“獨台”的理論表述。在“獨台”——即以承認現狀為特征的分離派——成為主流的氛圍中,你也可以說,現在的台灣政治仍然處於李登輝時代或李登輝時代的漫長陰影之下。 政治領域發生認同危機要更早,這確實跟中國大陸的變化關係很大。1989年政治風波對台灣和香港乃至整個世界的衝擊是不能低估的。陳映真在90年代初來大陸的時候,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是中共黨內的變化。從二十世紀的政治視野來看,如果大陸不再有社會主義理念,統一的政治基礎就動搖了,統一不僅僅是形式主權的問題,而且是民族解放的問題。1997年,我去中研院參加學術會議,陳光興拉我去參加台社的活動,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大陸身份”。那一次訪台期間,我也見到陳映真,看得出來他很孤獨,被“獨派”攻擊,被年輕一輩的左派疏離,甚至追隨者也在分崩離析。陳映真被孤立最初是因為1989,那時他公開發表文章為大陸辯護;這件事情變成所有人攻擊他的一個借口。他挺中國大陸不是基於一般中華主義立場,而是基於他從政治的角度對美國霸權、冷戰格局及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位置所做出的分析。大陸的政治家關心統一,卻不明白存在完全不同的對於統一的理解,他們的統一觀也是“去政治化的”。陳映真就說,他被邀請參加人民大會堂的宴會,與那些當年參與迫害他們的人同桌共飲,就像被拉郎配一樣。而實際上,官方更加重視那些擁有政經權力的右翼。 1996-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適逢香港回歸時刻,大陸的主管方面漸漸疏離了長期為中國的解放事業而鬥爭的左翼,轉而將香港的幾個企業大佬作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對象。今天香港的危機與這個路線的轉變是相互關聯的。 時代發生了變化,固守冷戰時代的敵我定位已經不合時宜,統一戰線需要打破原有的階級邊界,團結各種能夠團結的力量,形成新的政治。但這個打破邊界的過程如果不是基於對矛盾及其轉化的分析,而是否定或遮蔽矛盾,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機會主義的陷阱。這個陷阱也就是接受“歷史終結論”,放棄對新的社會道路的探尋。真正讓陳映真感到孤獨的,是他到了大陸以後發現他跟所有見到的大陸作家完全不能交流了。阿城有一篇文章講到他們在愛荷華,他調侃中國革命的發言惹得陳映真大怒。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1990年代,王蒙等在青島開一個環境與文學的會,陳映真基於他對資本主義生產與環境的關係的唯物主義解釋,對環境問題做了理論分析,結果遭到所有人的反對;張賢亮在會上說:寧夏最歡迎大家去“污染”(投資即有污染)了。從青島回到北京後,陳映真約我見面,感慨良久。作為左翼統派的代表,他的憤怒不僅產生於政治立場的隔膜——在這方面,反而是自以為脫離了“政治立場”的大陸作家或知識分子更加重視“政治立場”,更習慣於黨同伐異。他的憤怒中包含了一種對政治地基變動的感覺。陳映真對歷史變遷的敏感遠非他的大陸同行能夠理解。他看到這個地基一天一天地被瓦解掉了,他帶著憂患之心反思自己經歷的時代,而他的大陸同行卻歡天喜地。 |
|
|
相關新聞:
- 大陸對台政策穩定務實 力促和平發展 (2015-01-30 08:33:32)
- 民進黨想要怎樣的兩岸關係? (2015-01-22 09:22:17)
- 朱穗怡:島內新局勢 兩岸新挑戰 (2015-01-12 09:22:17)
- 雙橡園升旗傷馬英九,如何任由評說? (2015-01-09 09:41:58)
- 雙橡園升旗掀蝴蝶效應 兩岸山雨欲來 (2015-01-08 08:57:29)
- 兩岸關係發展路向也是螺旋式上升 (2015-01-01 08:35:50)
- 蔡逸儒:台灣九合一選舉後的兩岸關係 (2014-12-30 09:41:07)
- 朱穗怡:兩岸和平基石不可動搖 (2014-12-29 10:06:43)
- 朱立倫任黨魁後在兩岸關係走什麼路線? (2014-12-18 09:03:36)
- 選後陳德銘隨即訪台具有多重意涵 (2014-12-11 09:12:40)